老早的時(shí)候,我有個(gè)朋友寫了一篇文章,以金庸小說為例,探討武俠小說中的武功秘籍情結(jié),他用法國(guó)詩(shī)人馬拉美的詩(shī)句“世界的存在是為了一本書”做了這篇文章的題目。當(dāng)然,馬拉美的本意,是說表達(dá)的神秘和復(fù)雜,所以這句話還有一個(gè)版本:“世界萬(wàn)物的存在都是為了落腳在一本書里”。不過,用書來探討人和世界的關(guān)系,是紙書時(shí)代的事,現(xiàn)在,伴隨著紙書消亡的(或許也是書的消亡),是越來越強(qiáng)烈的不自信,武功秘籍,越來越少出現(xiàn)在武俠小說里了,當(dāng)然,這或許是故事類型更新的需要,卻也許就是書消失的前兆。
所以,這幾年,我一直想套用《西游記》的結(jié)構(gòu),寫一個(gè)奇幻故事:未來的世界里,已經(jīng)沒有書了,人們遇到了毀滅性的麻煩,不知如何應(yīng)對(duì),于是派人回到亞洲腹地,尋找一個(gè)神秘的、被火山灰掩蓋了數(shù)千年的圖書館,在那里尋找解決麻煩之道。或許,這還是紙書時(shí)代的思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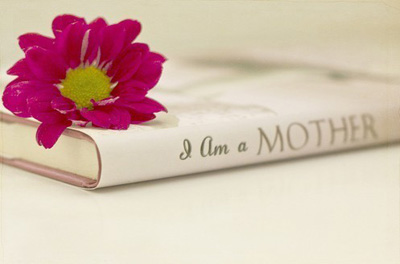
梁文道的《我讀》系列,還是更偏重于探討文字之美,對(duì)中文寫作的現(xiàn)狀有清醒的見解,有時(shí)候不過寥寥數(shù)語(yǔ),卻如千斤橄欖:“如今大陸很多人寫的中文都是被嚴(yán)重污染的中文,不要說寫,就是平常嘴巴里講的中文也是被污染的。隨便舉個(gè)例子,有時(shí)候看電視上一些大學(xué)者說話,他們說‘這件事的可操作性就很低了’如果用純正的中文,說‘這件事不好操作’就行了,不需要講個(gè)‘可操作性’。”書里說村上:“村上其實(shí)是以普魯斯特為榜樣,喜歡進(jìn)入內(nèi)心的記憶世界探險(xiǎn),但兩者的截然不同之處在于村上的書不會(huì)呆板無(wú)趣。你可以像讀昆恩的偵探小說一樣一口氣讀完,是適合這種高度商業(yè)社會(huì)的,低膽固醇時(shí)代的清淡型普魯斯特。”
梁文道的文字,有他一向的清平機(jī)智,是平白的,卻是準(zhǔn)確的,不過分拗著一股勁,卻也沒有寫疲了的人常有的那種四肢攤開似的無(wú)所謂。而且,《我讀》里的文字,是《開卷八分鐘》的講稿,所以是可以誦讀的,和《常識(shí)》、《我執(zhí)》的嚴(yán)肅正襟,又別有不同。
這種態(tài)度,表露的還是他對(duì)書的態(tài)度,在紙書消亡的年代,不驚慌,不憂懼,依然執(zhí)著于文字之美,試圖企及讀與寫的最高境界,像被刀劍指著的阿基米德,頭也不抬地說出“不要弄壞我的圓”。書評(píng)人唐山說,梁文道只能在大陸成為文化人,是因?yàn)?ldquo;大陸社會(huì)正在轉(zhuǎn)變中,人們背叛了一個(gè)意義,但仍或多或少相信,意義是存在的,這份執(zhí)著與尊重還沒有被商品化破壞殆盡,所以仍會(huì)乞靈于‘更成熟’的社會(huì)的文學(xué),相信它們中有一份特別的感受。”在綠洲逐個(gè)消亡的時(shí)候,尋找下一個(gè)綠洲,對(duì)新的寄身之所并無(wú)不安,這需要勇氣。
但那又不是作協(xié)官員式的并無(wú)不安,他們之所以神情泰然,是因?yàn)閷?duì)“書”與“寫”本身并沒有多少信仰,所以對(duì)它的消逝也并無(wú)憂慮,他們隨時(shí)可得華麗轉(zhuǎn)身。梁文道有一種被憂慮浸透之后的“我信”,“我讀”,就是此時(shí)此刻最好的信仰方式。
發(fā)表評(píng)論